上野千鹤子《厌女》语录集锦 - 知乎
1.不过,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换个更浅显的说法,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有一次也没有庆幸过没生为女人的男人吗?有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生为女人吃了亏的女人吗?
2.巴甫洛夫的狗,只要对方是女人,无论是谁就都能发情,对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性器官甚至女人的符号或片断的肢体部位,都会条件反射地自动发生反应。其实,他们反应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符号。如若不然,是不可能把所有女人都溶人“女人”的范畴之中的。看来,男人的恋物癖欲望的身体化程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使是片断的女性符号,也会轻易而迅速地发生反应,就如自动机器一般。为避免误解,应该再说一句,恋物癖并非动物本能,而是高度的文化产物。连巴甫洛夫的狗,也是“学习”规则的结果。
3.奥本一语道破了好色男人的厌女症。“好色男人的厌女症”之谜,应该如何解释呢?是否可以说,因为他们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不得不依赖他者女人这一悖论非常敏感?换个说法是,每一次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男人时,都不得不依赖女人这种恶心污秽不可理喻的动物来满足欲望,男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怨与怒,便是厌女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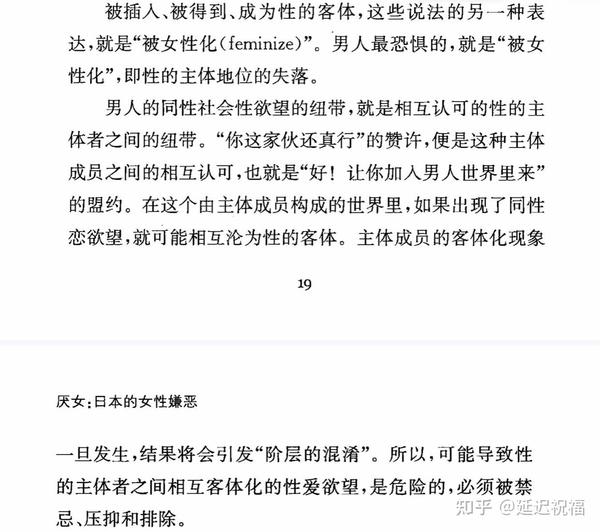
4.女人被男人当作发泄郁闷愤怒的垃圾场,可如果那是女人自己想要的,甚至还很享受,男人就不必背负罪恶感了。而当女人“不再痛苦,发出欢喜的呻吟”时,男人又在心中感叹,“女人这东西真是妖怪魔物”。由此将女人放逐到未知的世界里去。这样,男人便把女人双重地他者化了。
5.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这种结构手法非常好懂。首先,“是女人先勾引我,可不是我的错”。男人的欲望由此得以免责。然后,即便是把不情愿的女人强行推倒在地的强奸,最后还是以女人的快感结局,仿佛在说“怎么样,你不也有快感了吗?”好像女人的性器是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和暴力都转换为快感的无底黑洞。为男性读者制作的色情文学,最后终极点不是男人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这个现象看似矛盾,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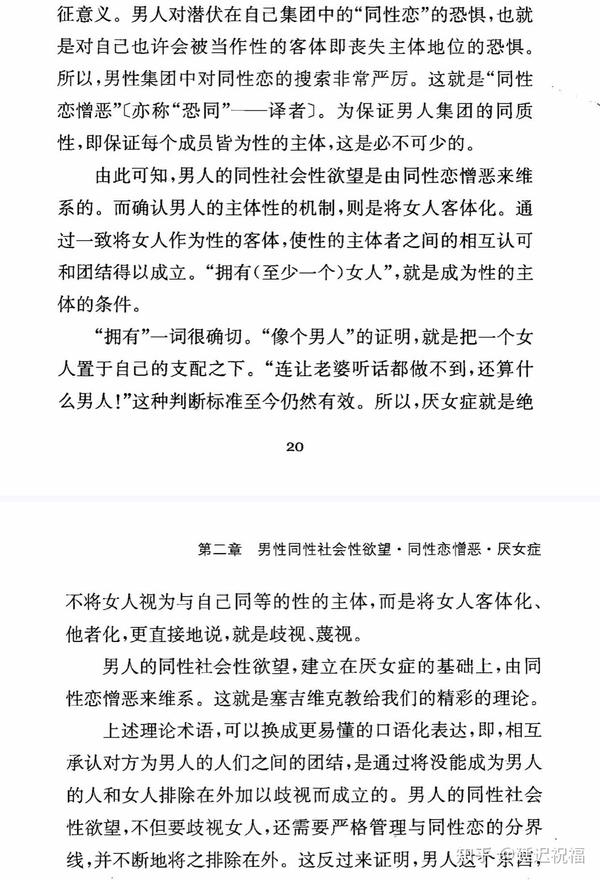
6.在一个阶级和性别严格分界的舞台装置之中,对挣扎在苦海中的女人表达同情、聆听她们的不幸身世,便成为身处绝对安全圈之内的人们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即便这样,有时也不过是逢场做戏。娼妓根据客人爱好编制各类身世故事讲给客人听,让客人当“好人”,给客人“增值”,这实为一种广为人知的商业行为······
7.水田说,近代男性文学中的<女人>(并非真实的女人而是作为恋物癖符号的女人,故加尖括号),是构成男人内心世界的私人空间。男人为逃避公共世界而寻向<女人>这个空间,可在那里遇到真实的女人,发现对方是不可理喻令人不快的他者,于是又从那里尝试再次逃离。这种逃离,是“逃离家庭”还是“逃往家庭”,则因时、地而定。“逃离家庭”很容易理解,但逃离之后,他们发现的是不能满足他们梦想的另一个他者,于是又再次逃离。
8.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不但要歧视女人,还需要严格管理与同性恋的分界线,并不断地将之排除在外。这反过来证明,男人这个东西,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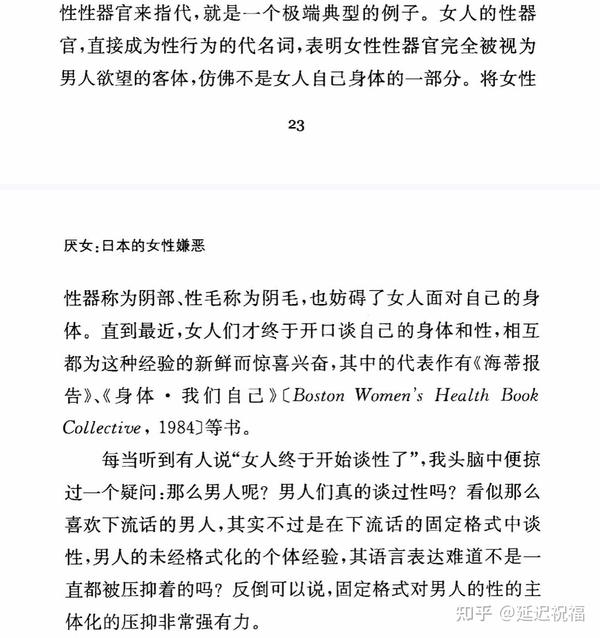
9.男人那么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当我们叹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即,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
10.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 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 与“内行女 人(性行业中的女人)”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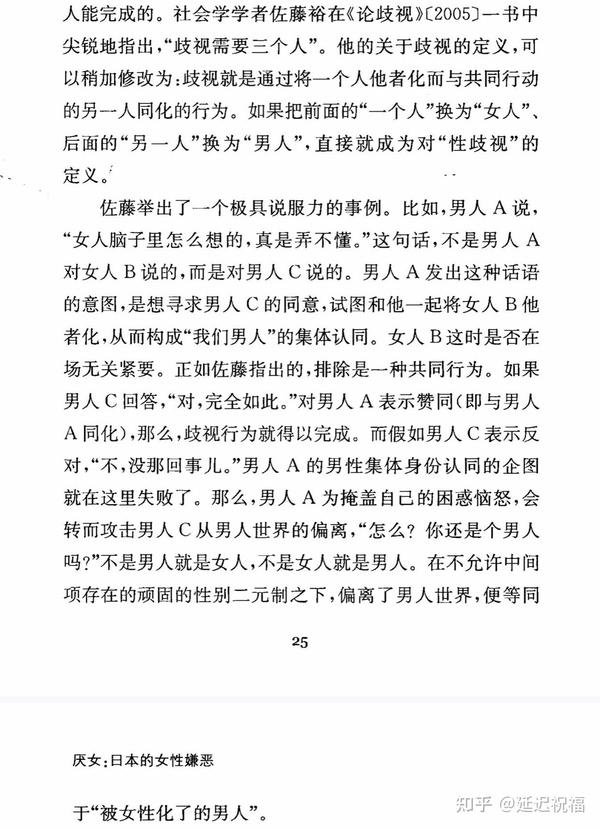
11.换言之,“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们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赤裸裸地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们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人的骄傲,悯笑“行外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软弱。
12.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性交吗?性交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阳痿男人,与前面那位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她的反应的人,勃不起来;而当对方是无需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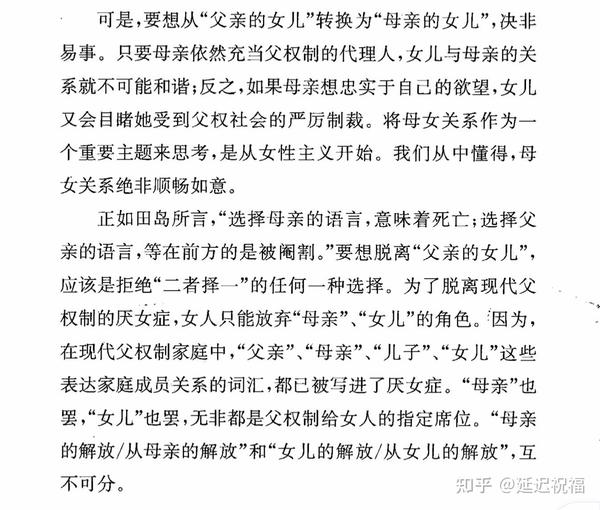
13. 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将娼妓赎身迎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
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地区,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直住在娘家,搬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然后才带着继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过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14.那么,我想问问他:既然想被养起来,那女人迄今为止在家庭中承受的一切,包括家务劳动、抚育儿女、护理老人、性的奉献、家庭内暴力,都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吗?可他对此没有提及。“主夫”很少,不仅因为具备供养主夫的经济能力的女人很少,还因为愿当主夫的男人很少。这不过是因为,男人们早已知道,不仅主妇,主夫也是处于不利位置的。
15.赤木出示的不等式为:强者男人(工作+)>强者女人(工作+、 家务- )>弱者女人(工作-、家务+)>弱者男人(工作-)。在这个奇妙的不等式中,“弱者男人”居于最下位。

16.总之,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一般来说,被称为“性弱者”的男人,由于没有与女性的现实接触,他们关于女人的固定观念与现实完全脱节,几乎达到妄想的程度。
17.最不能定型化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没有利害得失、角色分担不固定、不能期待从中获取直接利益,正因为如此,没有比朋友关系更难以维持的了。正如深泽真纪在《不消磨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维持方法》一书中所言,朋友关系是“人际关系的高级篇”。维系朋友关系需要高度的技能,或许比恋爱结婚还难。因为在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中,双方只需扮演一种固定的角色。
18. 全美性教育信息协议会(SIECUS)所下的定义:性欲 (sexuality)不是存在于“两腿之间(between the legs)”,而是. 存在于“两耳之间(between the ears)”即大脑之中。所以,性欲研究(sexuality studies) 其实不是关于下半身的研究。
不过,这种作为舞台装置的幻想也不能说是完全个人的东西,其基础是文化中既有的现成脚本,在现成脚本的基础上添加个人色彩,就形成了个人的幻想。所以,我的《发情装置》一书,加了一个副标题“色情的脚本”。即使性欲望伴随的幻想是一种对恋爱关系的想象,因为欲望本身是在个体内部完结的,所以,“我爱你与你毫无关系”的说法是成立的。在这个范围内,欲望,与想象力一样,是自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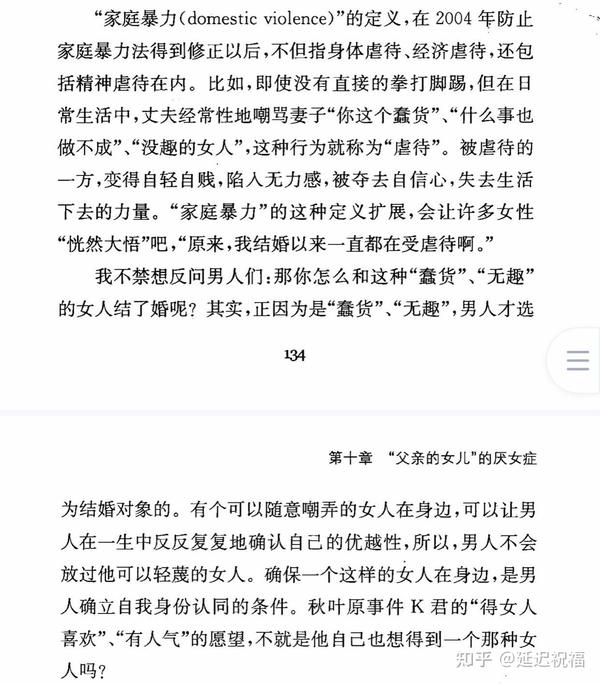
19.没有对方的同意,即使夫妻之间,“强奸罪”也可以成立;让对方不愉快的性接近,可视为“性骚扰”。迄今为止,这些行为都在“私”的名义下被封闭起来了。性关系根本不是“私”,是两人以上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按照麦克尔等人的说法,所谓“私”,应该完全限定在个人世界之内。
20.美国的女性主义者罗宾·摩根(RobinMorgan)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色情制品是理论,强奸是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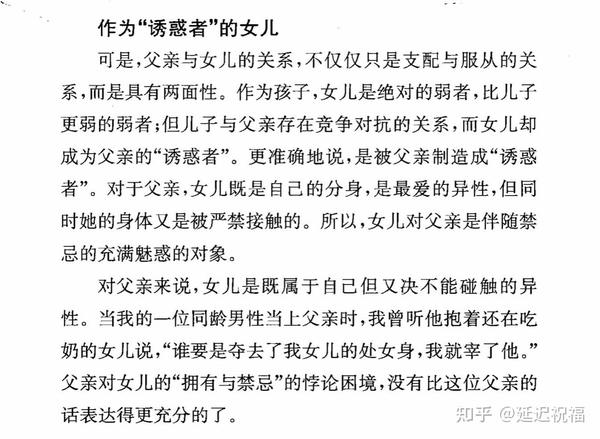
21.被害者希望,加害者至少能够意识到自己给对方带来的伤害,可加害者,却总想过轻地看待被害者受到的打击,甚至还故意错觉被害人是自己情愿的。其实,这反过来证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有罪恶意识的。他们对自己是加害者这一事实是有自觉的,所以,才会有意识地把“凯蒂和我性交的时候”换为“也许该说是我对凯蒂性交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还剥夺了对方的反抗,他们对此是自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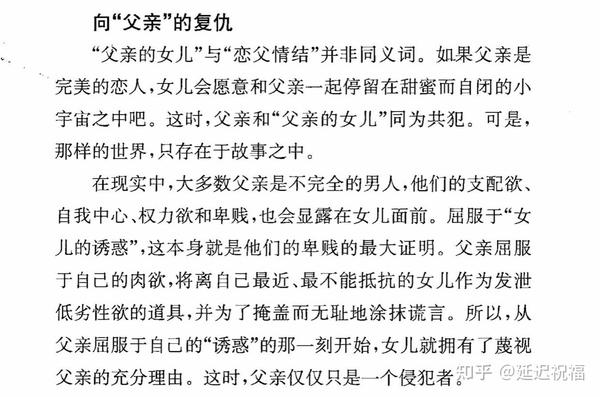
22.事实上,媒体形式的性产业,都是辅助自慰的性幻想装置,在二元平面的色情游戏、美少女漫画中,旧态如故的男权主义性幻想被再三地重复生产,在那里,女人作为诱惑者,主动顺从男人的欲望。即便如此,从虚拟世界的符号得到满足的“对二元平面发情”的宅男和草食系男子们,也比胁迫“让我干”的野蛮的“肉食系”男子好。想象力是不能被取缔的,只要他们没有付诸行动。
23.与此相比,经济能力为更上位的资源。因为经济能力不但比暴力和权力更为安定,还具有更广泛的通用性。只要有钱,暴力和权力都能买到。身体衰弱的老人,可以用钱雇保镖;无能之辈,可以用钱获得地位,至少在从前,钱权交易更公然无忌。
24.无论在社会上处于多么弱势的位置,只要能在性方面支配女人,便可以扭转其他一切负面因素——男人的这种信念十分顽固。在色情制品中,这一点体现得非常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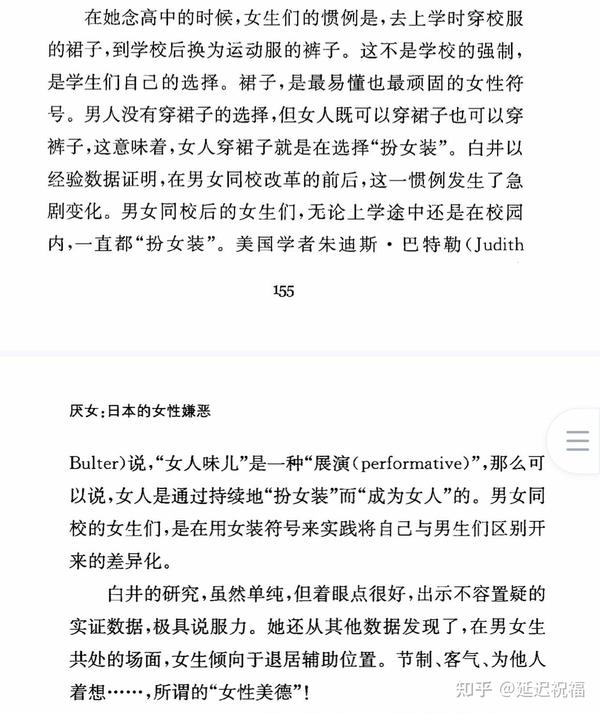
25.“生女儿更能轻松地享受育儿的乐趣”的想法,反过来证明了养育孩子的负担之沉重。与此相反,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将来可能收回投资成本并从中获益的手段)”的社会里,生男选择还会跋扈横行。对于日本皇室,男孩显然是“生产资源”。
26.“有女朋友”,指的是将一个女人据为己有的“拥有”状态。即使其他所有要素都欠缺,只要有了这最后一个要素即拥有一个归己所有的女人,便能满足男人之为男人的最低条件。反言之,即使学历、职业、收人等其他一切社会条件都很优越,但却“连一个女人也弄不到手”这种男人的价值就会降低。男人集团绝不会承认这样的男人为一个成年男人,绝不会给予他这个集团的正式成员资格。这就是雄“败犬”比雌“败犬”更难承认“败”、处男比处女更难启齿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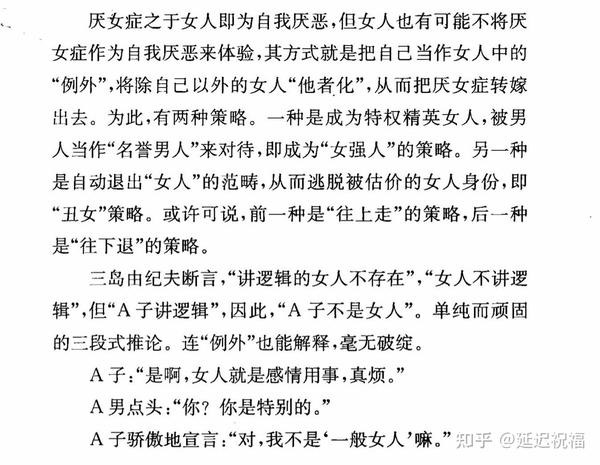
27.日本这个国家,就这样建立在皇族女性同时也是皇族男性的牺牲之上。天皇主义者们,说不定在心想:为了捍卫天皇制,必须让“陛下”成为牺牲品,不能允许陛下的“任性”。不知天皇主义者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任意践踏背负着皇室招牌的家族成员们的人权。同时,只要我们还称之为 “皇室家族( Royal Family)”,并作为国民的家庭范本,那么,日本社会就还不能从深植于皇室中的厌女症得到自由和解脱。
28.“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小仓千加子一语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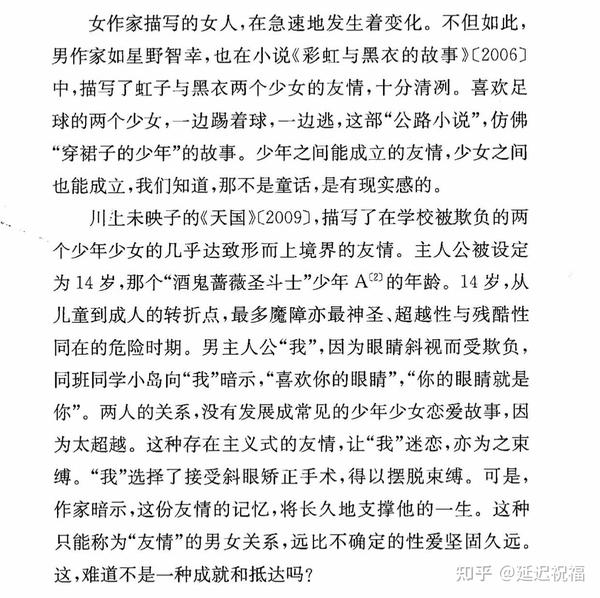
29.女人的嫉妒指向夺去男人的别的女人,而男人的嫉妒则指向背叛了自己的女人。因为女人的背叛是对男人所有权的侵犯,建立在占有一个女人的基础上而得以维系的男人的自我,会因此面临崩溃的危机。对于女人,嫉妒是以其他女人为对手围绕男人展开的竞争;而对于男人,嫉妒则是维护自尊和自我确认的争斗。
30.既非暴力支配,亦非权力支配和财力支配,而是“性力”支配,并且让被支配方自发服从,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恐怖的支配,而是通过快乐的支配。这才应称为终极的支配吧。我们知道,权力论的要义是,自发的服从才能降低支配成本从而使支配安固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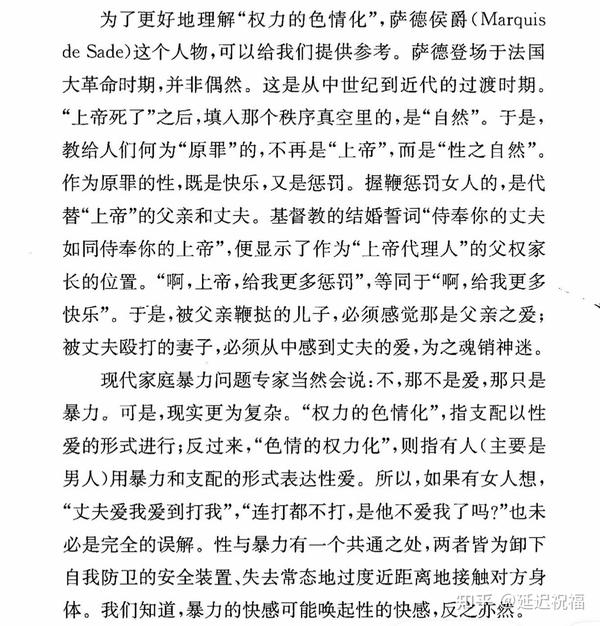
31.我们知道,江户时期的春宫画是“属于男人、来自男人、为了男人”的性消费品,那么,“和睦同乐”作为春宫画中的一种固定模式,应该视之为“这么干女人会喜欢”的男人幻想的投影。
32.男根被置于快乐的中心地位,这在描绘女性同性恋的春宫画中也可以看到。我已经说过多次,但还是要再次重复:男根为快乐的中心是男人的幻想。春宫画中有描绘女人的自慰和女人之间性行为的场景。有这样一种图式,一个年轻 姑娘或女佣,一边偷看主人或其他男女的性交,一边玩弄自己的性器。这里描绘的,是被异性恋触发的女人的欲望,由此暗示:自慰为得不到“正常”性交满足时的替代行为、性欲的终点应该是有对象的性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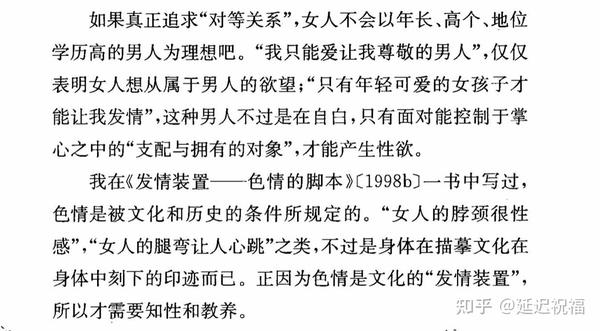
33.生我养我、不惜辛劳地抚育我、作为人生最初的强者伫立于我面前却又侍奉更强的丈夫、为了我忍受来自丈夫的一切苦楚、主动承受一切牺牲、接纳我的一切....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去侮辱呢?这个可称为自我的无条件的“存在依据”的女人。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女人,这种母亲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不过,“母亲”这个范畴所具有的“规定性”,束缚着儿子,也束缚着女人本身。
34.回顾历史,比起父母亲一代,孩子一代在整体上生活水准和教育水准都提高了(换言之,这一代作 为一个整体比父母亲一代“ 有出息”),但这是时代所致,并非个人努力或能力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女性,脱离出身阶层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结婚。当女性作为“妻子”失败之后,便作为“母亲”期待儿子超越父亲。于是,儿子们从小就听母亲像唱催眠曲一般念叨“你跟你爸爸不一样,你.....”,他们被迫担负起对母亲怎么也还不尽的巨大负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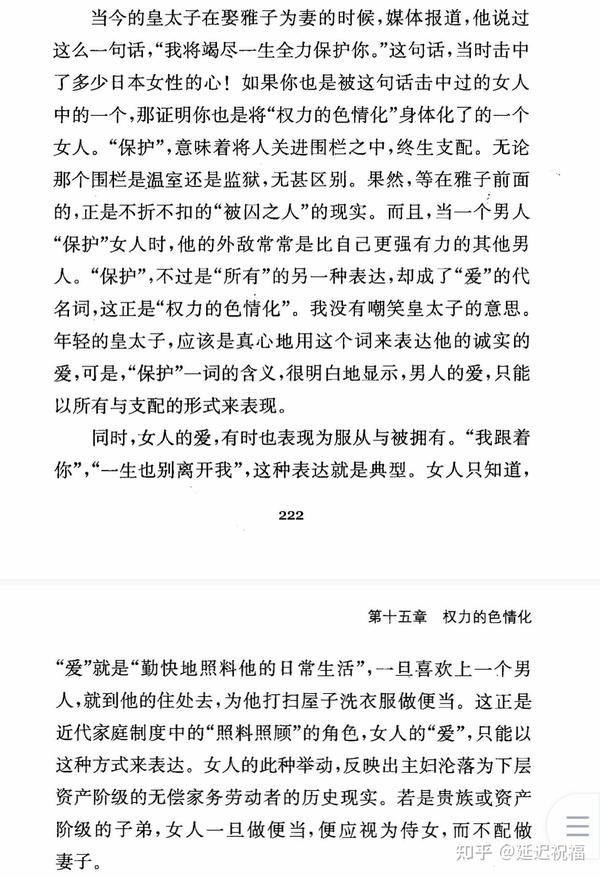
35.江藤将“女性的自我厌恶”称为“‘近代'给日本女性植人的最为深刻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自我厌恶,可以说是所有生活在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女性的普遍性情感。”
36.只有当“都是一样的人”这种可以公约的“分母”出现之后,“歧视是不应当的”的心性才会产生。性别歧视本身,并非从前不存在,但“近代”通过“比较”反过来将这种歧视强化了。所以,控诉性别歧视的女性主义,是作为近代社会的直接后果而诞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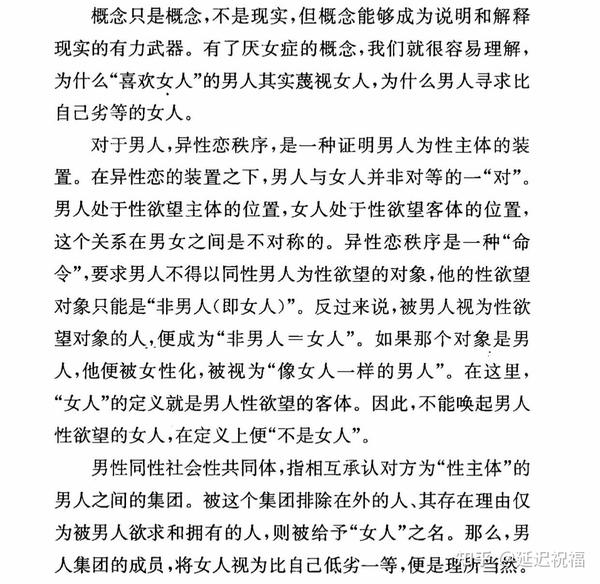
37.我发现,被视为“女人味”的要素,比如“节谨”、“娴静”,等等,与“忧伤”何其相似。换言之,自我欲望的意识与实现,在出生之前便已受阻,这种存在就是“女人”。倘真若此,生为女人,多不合算!
38.可是,女人赋予女人的价值,与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相比,位居次等。酒井把没结婚的女人称为“败犬”,背后便有这种意识。即,女人有两种价值,一种是靠自己挣来的,另一种是被他人(=男人)赋予的,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所以,没结婚的女人被称为“败犬”。因为,结婚是女人被男人选上的登记证。
39.学业分数被期待为对“女性资源”匮乏的弥补。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少女,则试图以“女性分数”的“替代资源”来立于学业优秀的女生之上。对成绩好的女生,她们嘲笑其“女性资源”的贫乏,挖苦她们是“丑女”“不懂男人”,同时她们自己积极地向时装化妆品等“女性资源”投资。不过,“女性分数”不是靠自己挣来的,归根到底是被男人选择(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男人赋予的价值,所以,思春期的少女们走向性早熟的行为,越出学校文化的规范。由此,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貌似反抗学校文化的早熟少女,却成为男人社会里始乱终弃的性的客体。
40.“山姥假皮”就是“让女人接受"的变身道具,因为女人绝不宽恕被男人喜欢的女人(无论她本人是自觉或不自觉)。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数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建立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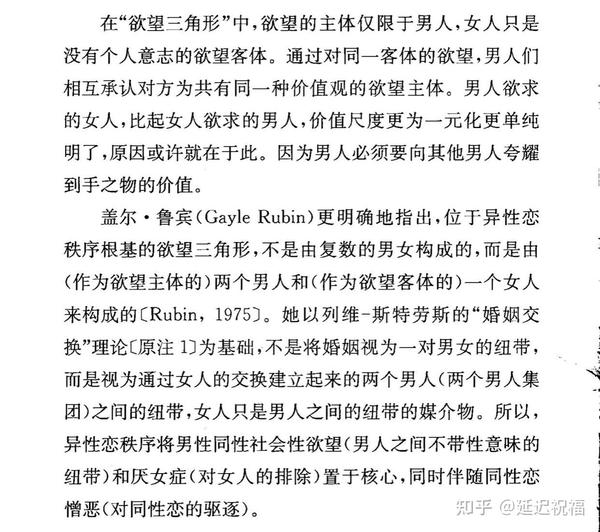
41.佐野用“堕落”一词,是基于一种长久以来的旧式思维,即,女人出卖自己的性是有悖人伦的行为。同时,“堕落”一词还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忽视。
42.学业能决定在集团中的序列名次,只是在女校这种牧歌般的封闭空间之内。一旦走出这个女人集团一步,男人的视线便如物体的重力一般,无所不在,弥漫于整个空间。
43.在作家的视线背后,是一种自虐或批评意识吗?我很怀疑。看她描写女主人公的毁灭时毫不留情的笔致,我感到的是作家通过将自己视为“例外”而拥有的一种“外部”视线,作家以这种特权的外部视线刻毒地观察着女主人公。若是自我批评,必然会伴随一种苦涩,但这种苦涩感在作家身上过于稀薄,使我只能感到她的恶意。男作家或许还会对女人抱有一分幻想,女作家连幻想也没有,所以,厌女症更为彻底。
44.所谓“妒恨”,是最终不可能超越对方之人所怀有的、虽然并非无害、但也不构成威胁的一种心理状态。通过将自己置于“例外”,林真理子得到了把“妒恨”安全地商品化的位置。读者可以一边嘲笑作家,一边安心地处于恶意之中。当然,林真理子的位置,并非她的真实状态的反映,而应该是她周密地用心选择的一种策略。
45.自从性被隐私化以后,“关于隐私”,就成为“关于性”的代名词。家庭,成为“性家庭”;夫妻,成为“性的纽带”的代名词;婚姻,成为性行为的社会许可证;“初夜”,宣告性关系的开始;“无性”,被视为夫妻关系的“病理....我们今天熟知的关于婚姻与夫妻的“常识”,由此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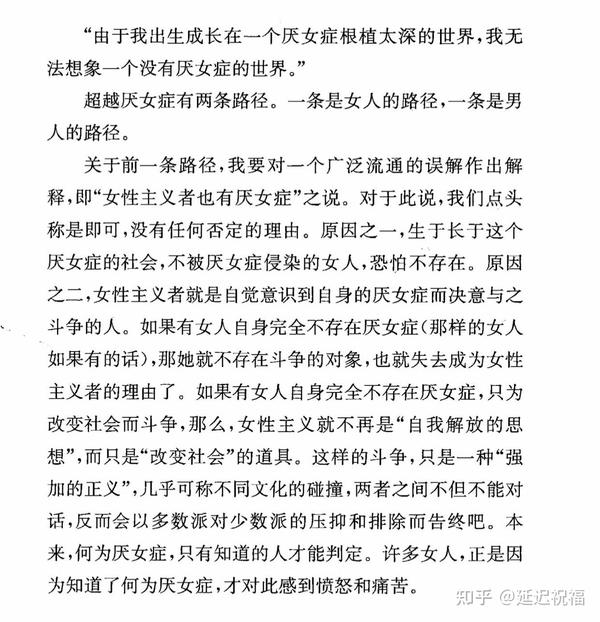
46.一对夫妻成为性别关系的象征,是近代社会-夫-妻的婚姻制度确立以后的现象。在重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中,婚姻完全不是对等的关系,连“对偶”关系也不是。妾,是仆人身份,即缔结了专属合同的性工作者。对于日本的妻子,长久以来,性是“奉献”,是不能说不的“任务”,不是什么快乐。要是那些妻子知道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规范是“性快乐的权利与义务”,她们会怎么反应?真险,我差点儿就要说出“资产阶级社会在日本从未成立过”之类的话了。
47.我一直以为,男人是在与女人的“对偶”的关系中“成为男人”的。错了。男人是通过与男人集团的同化而“成为男人”的。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是其他男人;承认一个男人“成了男人”的,也是其他男人。女人至多不过是男人“成为男人”的道具,或作为“成了男人”的证明伴随而来的报酬奖赏而已。与此相反,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是男人;证明一个女人.“成了女人”的,也是男人。
48.所谓女人,是对“非男人的人”标注特征的名称。这个群体被划人另一个范畴,其特征必须与被视为属于男人的一切美德与名誉区别开来。女人与男人不同,是“不勇敢的人”,“不坚强的人”,“没有领导决断能力的人”,“懦弱的人”,“小心谨慎的人”,“无能的人”,一言蔽之,“不能成为主体的人”。所有这些“女人属性”,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适合成为男人支配对象的属性。
49.周刊杂志《AERA》(2010年5月3日号)对封面人物韩国影星李秉宪(LeeByunghun)的采访文章。“我想远离比我还能喝酒的、我说不过的女性。因为女性我想自己来保护。”“好像能把身边的男人都打败似的女人,很恐怖,不太喜欢(笑)。”他的这些话,等于在坦白:在女强人面前,他就会阳痿。他的“女性我想自己来保护”一语,不过是“占有”欲望的委婉修辞而已,实质是把比自己劣等的女人围人自己领地之内的赤裸裸的占有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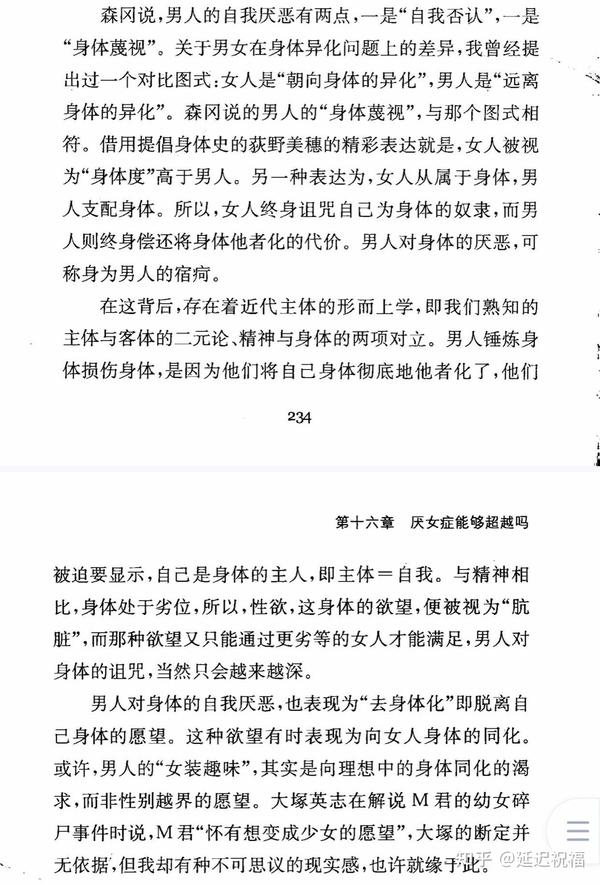
50.森冈指出的男性的自我厌恶,的确有深度,触及到了男性性的根基。他谈到了男性性与暴力的结合。暴力,以恐怖为名,是一种解除了自我防卫的与他者身体的过剩关系。男人在与他者身体发生暴力关系以前,应该先是对自己身体的暴力吧。这一方面表现为不顾身体安全的鲁莽或勇气,另一方面表现为酒精中毒、毒品中毒等慢性自杀。对身体的过度关注,被视为“懦弱”、“像个女人”等男人气的欠缺。无论走向哪一方,等在男人前面的,都是“自我厌恶”。可以想见,对于男人,无论“是男人”或“不是男人”,都是充满痛苦的经验吧。
51.将自己标高价出售的女人,是承认买自己的男人有与那个价格相当的价值;把自己廉价贱卖的女人,则是认定男人只有那个价;不要钱跟谁都干的女人,等于把自己身体“扔进 阴水沟" ,她们以此来验证,男人的性欲也就是“扔进阴水沟”一般的东西。
52.一面将女人还原为性器官,一面又不得不依赖女人来满足欲望一对男人性欲的这种作茧自缚的构造,最诅咒的是男人自己吧。
53.正因为男人的性欲对“迷你裙”、“裸体”甚至性器官等片断的肢体部位也能发生条件反射,性买卖才得以成立。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男人的性欲就像被称为“兽欲”一般,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男人的性欲是如此被条件规定了的文化产物。买娼的男人,买的不是女人,而是女人这个符号。正因为男人是在对符号发情,对符号射精,所以,买娼才是自慰行为之一种。那么,卖娼的女人,卖的又是什么呢?卖的是“成为物品的自己”(或者说“成为他人所属品的自己")。通过“成为物品”,女人将向“物品”射精的男人解体还原为仅仅的性欲。由此,男人憎恶娼妓,娼妓轻蔑嫖客。